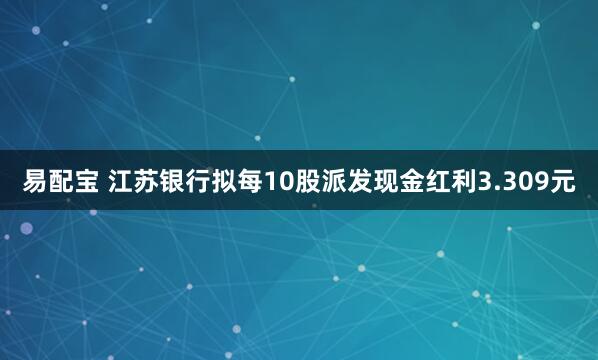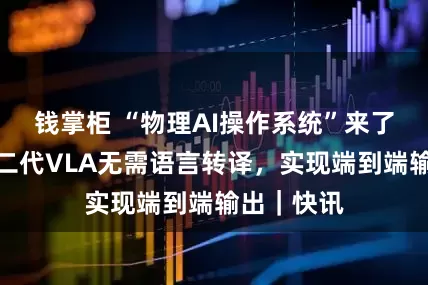元宝枫资本 《春日旷野的风筝,牵着岁月的风与牵挂》

衣柜顶层的收纳箱里,那只菱形风筝正叠在碎花布下。绢面蒙着层薄尘元宝枫资本,却依旧能看出当年鲜艳的红,边角的流苏已有些磨损,竹骨却依旧挺括,线轴上的棉线缠绕得整齐,末端还系着个褪色的蝴蝶结 —— 这是父亲在我十岁那年亲手扎的,当时他用竹篾细细打磨骨架,笑着说 “等春风起,咱们就去放风筝”,却没料到这只风筝,会陪着我走过二十个春天,把童年的奔跑、父亲的陪伴、旷野的风,都悄悄系进了细细的棉线里。
第一次见风筝飞起来,是个晴朗的春日午后。郊外的旷野上,春风裹着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,父亲把风筝展开,我蹲在一旁帮他递线轴。“风筝要顺着风放,手要稳,等它往上飘的时候再慢慢放线”,父亲握着我的手,教我调整姿势。起初风筝总在地上打转,绢面被风吹得簌簌响,我急得额头冒汗,父亲却耐心地帮我重新整理竹骨:“别急,风是风筝的朋友,咱们等它愿意带风筝飞的时候。” 忽然一阵风来,父亲轻轻一托风筝,“快跑!” 我拽着线轴往前冲,回头时,那抹红色已摇摇晃晃地升上天空,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在蓝天上越飞越高。风从耳边掠过,线轴在掌心轻轻震动,父亲的笑声混着风声传来,“看,它飞多高!” 那天的旷野上,风筝牵着棉线,也牵着我雀跃的心,成了我关于春天最鲜活的记忆。
风筝的绢面与竹骨间,藏着无数个关于春日的印记。绢面边缘的缝补痕迹,是我十二岁那年弄破的 —— 当时风筝被风吹得撞上树梢,绢面刮破了个小口,我蹲在地上急得快哭了,父亲却从口袋里掏出针线,当场缝补:“没事,补好的风筝更结实,还能接着飞。” 现在摸着那几缕细密的针脚,还能想起父亲低头缝补时,阳光落在他发间的模样;竹骨末端的浅痕,是常年与线轴摩擦留下的,父亲每次收风筝前,都会用砂纸轻轻打磨竹骨,“这样下次飞的时候,不会勾破绢面”,那些磨得光滑的竹骨,像藏着父亲的细心;最特别的是线轴上的刻字,是父亲用小刀轻轻刻的 “追风”,当时我不懂什么意思,后来每次握着线轴,看着风筝在风里舒展,才明白父亲是想让我像风筝一样,既有乘风的勇气,也记得线的牵挂。
展开剩余55%它最 “热闹” 的时候,是每年的清明前后。父亲会带着我和邻居家的孩子,去郊外的旷野放风筝。孩子们举着各自的风筝奔跑,风筝在天上争着向上,有的是彩色的蝴蝶元宝枫资本,有的是展翅的老鹰,而我的红风筝,总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有次邻居家的小宇风筝线断了,看着风筝飘向远方,他急得哭了,父亲却笑着把我的风筝线递给我们:“来,咱们一起放,一只风筝也能载两个人的快乐。” 那天我们轮流握着线轴,风筝在风里飞得更稳了,笑声在旷野上飘得很远,连风都带着甜意。
风筝也曾 “闲置” 过,是在我上高中之后。学业渐渐繁忙,春日的旷野成了难得的念想,风筝被我叠好放进收纳箱,一放就是好几年。有次整理衣柜,我翻出落了尘的风筝,竹骨依旧挺括,绢面却有些泛黄。父亲看到了,笑着说 “走,咱们去郊外走走”,那天我们没让风筝飞起来,只是坐在草地上,把风筝摊在膝头,父亲给我讲他小时候放风筝的故事,风轻轻吹着绢面,像在回应我们的絮语。
现在这只风筝,依旧放在衣柜顶层的收纳箱里。去年春天,我带着女儿回娘家,翻出风筝教她辨认:“这是爷爷给妈妈扎的风筝,以前妈妈总跟着爷爷来放它。” 女儿好奇地摸着绢面,“妈妈,我们也去放风筝好不好?” 我和父亲带着她去了郊外,父亲帮她举着风筝,我握着她的小手放线,当那抹红色再次升上天空时,女儿的笑声像极了当年的我。父亲站在一旁,看着天上的风筝,眼里满是温柔,风把他的白发吹得轻轻飘动,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重叠。
暮色漫进房间时,我把叠好的风筝放回收纳箱,绢面的红色在昏暗中依旧醒目。忽然明白,春日旷野的这只风筝,从来不是普通的玩具。它是时光的 “风筝线”,一头牵着童年的奔跑与笑声,一头牵着父亲的陪伴与牵挂;它是成长的 “见证者”,看着我从追着风筝跑的孩子,长成能牵着孩子放风筝的大人;它是情感的 “载体”,把春天的风、旷野的辽阔、家人的温情,都系在细细的棉线里,无论走多远,只要想起它,就能触摸到岁月里的温暖。
风从窗缝钻进来,吹动收纳箱的衣角,仿佛还在等着春日再次来临,等着我们牵着风筝走向旷野,等着把更多关于风与牵挂的故事,系进棉线里,永远留在每个明媚的春天里。
发布于:湖北省财盛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